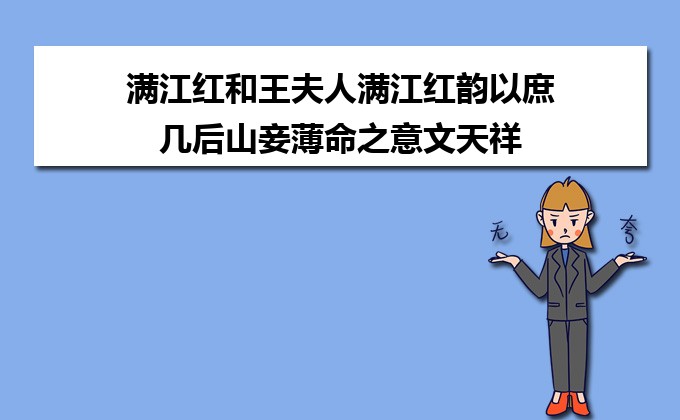ЗпИХікНхХСғxКЗЛОҙъНфФӘБҝөДФҠ(shЁ©)ЧчЈ¬ФҠ(shЁ©)ИЛФЪФҠ(shЁ©)ЦРҢҰ(duЁ¬)ТвПуөДс{сSЈ¬ҢҰ(duЁ¬)ҡvК·КцХf(shuЁӯ)•r(shЁӘ)өДДЗ·NҝvЙоёР¶јБГИЛРДПТЎЈ
ФӯОДЈә
ЗпИХікНхХСғx
ЧчХЯЈәНфФӘБҝ
іоөҪқв•r(shЁӘ)ҫЖЧФХеЈ¬Мфҹфҝҙ„ҰңIәЫЙоЎЈ
ьSҪрЕ_(tЁўi)АўЙЩЦӘјәЈ¬ұМУсХ{(diЁӨo)ҢўҝХәГТфЎЈ
Иf(wЁӨn)И~ЗппL(fЁҘng)№Вр^үф(mЁЁng)Ј¬Т»ҹфТ№Ук№Каl(xiЁЎng)РДЎЈ
НҘЗ°ЧтТ№ОаН©УкЈ¬„ЕҡвК’К’Ил¶МҪуЎЈ
Ҷ–(wЁЁn)о}Јә
ЈЁ1Ј©“іо”КЗЯ@КЧФҠ(shЁ©)өДФҠ(shЁ©)СЫЈ¬ФҠ(shЁ©)өДКЧВ“(liЁўn)ЎўоhВ“(liЁўn)КЗИзәОұн¬F(xiЁӨn)Я@·NқвіоөДЈҝ
ЈЁ2Ј©ФҠ(shЁ©)өДәуғЙВ“(liЁўn)К№УГБЛКІГҙұн¬F(xiЁӨn)КЦ·ЁЈҝХҲ(qЁ«ng)ҪY(jiЁҰ)әПИ«ФҠ(shЁ©)·ЦОцЧчХЯөДЛјПлёРЗйЎЈ
ЗпИХікНхХСғxйҶЧxҙр°ёЈә
ЈЁ1Ј©КЧВ“(liЁўn)НЁЯ^(guЁ°)Ң‘ХеҫЖЎўМфҹфЎўҝҙ„ҰЎўБчңIөИ„У(dЁ°ng)ЧчЙс‘B(tЁӨi)ұнЯ_(dЁў)іоҫwЈ»оhВ“(liЁўn)УГөдЈ¬Ң‘ҝХУРьSҪрЕ_(tЁўi)Ј¬НчХ{(diЁӨo)ұМУсёиЈ¬ұнЯ_(dЁў)ЧФјәөД№ВјЕг°җқЎЈ
ЈЁ2Ј©Зйҫ°Ҫ»ИЪөДКЦ·ЁЈЁҙрТrНР»тҪиҫ°КгЗйТІҝЙЈ©ЎЈоiВ“(liЁўn)Ң‘ЗппL(fЁҘng)Иf(wЁӨn)И~Ј¬ТrНРЖд№ВјЕұҜЗРЈ»Ң‘№ВҹфТ№УкТrНРҡwЛјлyҪыЎЈОІВ“(liЁўn)ТФҫ°ҪY(jiЁҰ)ЗйЈ¬УГОаН©Т№УкЈ¬ә®ҡвК’К’Ј¬ҳӢ(gЁ°u)іЙЖаЗРұҜӣцөДТвҫіЎЈИ«ФҠ(shЁ©)Кг°l(fЁЎ)БЛЙоіБұҜЗРөДНцҮш(guЁ®)Ц®Нҙ№Каl(xiЁЎng)Ц®Лј·ӯЧgЈә
‘nіоөҪқвБТөД•r(shЁӘ)әтДГҫЖҒн(lЁўi)ЧФХеЈ¬МфББҹф¶ЛПйҢҡ„ҰІ»УX(juЁҰ)ңIәЫТСЙоЎЈьSҪрЕ_(tЁўi)ЙРЗТРЯАўИұЙЩЦӘјәЈ¬ұМУсёијҙҢўЧФҮ@ҝХУРәГТфЎЈЗппL(fЁҘng)АпИf(wЁӨn)И~пh“u№Вр^өДүф(mЁЁng)лyіЙЈ¬Т№УкЦРТ»ұK»иҹфҶҫИЎЛјаl(xiЁЎng)өДРДЎЈЧтТ№АпНҘФәЗ°ГжөДОаН©ЛҪХZ(yЁі)Ј¬ДЗК’К’ә®ҡвҙөИлОТ¶МұЎТВҪуЎЈЧЦФ~ҪвбҢЈә
[1]Ў¶ФҠ(shЁ©)ңYЎ·өЪОеғФ(cЁЁ)ТэҙЛФҠ(shЁ©)Ј¬о}ҹo(wЁІ)“ЗпИХ”¶юЧЦЈ¬хUұҫЎ¶Л®ФЖјҜЎ·Таҹo(wЁІ)“ЗпИХ”¶юЧЦЎЈНхХСғxЈәГыЗе»Э(ХСғxКЗҢmЦРЕ®№ЩГы)Ј¬ДЬФҠ(shЁ©)ЎЈНфФӘБҝФЪ¶ИЧЪіҜТФЙЖЗЩұ»ХЩЈ¬јҙКВЦxәуЕcНхХСғxЎЈДПЛОНцЈ¬НфФӘБҝЕcНхХСғxҫгұ»“пұұИҘЈ¬әуНфФӘБҝһйөАКҝДПҡwЎЈЯ@ЖЪйgғЙИЛ¶аУРФҠ(shЁ©)ёиНщЯҖЈ¬Ў¶ЛОФҠ(shЁ©)јo(jЁ¬)КВЎ·ҫн°ЛК®ЛДҙжЗе»ЭФҠ(shЁ©)ЛДКЧЈ¬¶јКЗҢ‘ҪoНфФӘБҝөДЎЈ
[2]ьSҪрЕ_(tЁўi)Јә“ю(jЁҙ)Ў¶ЙП№ИҝӨҲDҪӣ(jЁ©ng)Ў·Ј¬ьSҪрЕ_(tЁўi)ФЪҪсәУұұТЧҝh–|ДПК®°ЛАпЈ¬СаХСНхЦГЗ§ҪрУЪЖдЙПЈ¬ТФСУМмПВКҝЈ¬ЛмТФһйГыЎЈЪуЈәхUұҫЎ¶Л®ФЖјҜЎ·Чч“Аў”ЎЈ
[3]ұМУсЈәЎ¶ҳ·(lЁЁ)ё®ФҠ(shЁ©)јҜЎ·ҫнЛДК®ОеТэЎ¶ҳ·(lЁЁ)Ф·Ў·Јә“ұМУсёиХЯЈ¬ЛОИкДПНхЛщЧчТІЎЈұМУсЈ¬ИкДПНхжӘГыЎЈ”ПжЈәхUұҫЎ¶Л®ФЖјҜЎ·Чч“Ңў”ЎЈ
[4]„ЕҡвЈәә®ҡвЎЈұіҫ°Јә
НхХСғxГыЗе»Э(ХСғxКЗҢmЦРЕ®№ЩГы)ЎЈНфФӘБҝФЪЛОД©№©·оғИ(nЁЁi)НўЈ¬јҙТФЗЩЛҮКВЦxМ«әуЕcНхХСғxЎЈЛОНцЈ¬НфФӘБҝЕcНхХСғxТ»Н¬ұ»М”ИЛСаЈ¬ҡvК®УаЭdЈ¬әуФӘБҝЖт?yЁӨn)йөАКҝДПҡwЎЈЯ@ЖЪйgНфЎўНх¶юИЛ“ЗЩ•шПаЕcҹo(wЁІ)М“ИХ”(НхЗе»ЭЎ¶ЛНЛ®ФЖҡw…ЗФҠ(shЁ©)РтЎ·)Ј¬¶аУРФҠ(shЁ©)ёиіӘәНЎЈЎ¶ЛОФҠ(shЁ©)јo(jЁ¬)КВЎ·ҫн°ЛК®ЛДКХУРНхЗе»ЭәННфФӘБҝікЩӣ(zЁЁng)ФҠ(shЁ©)ЛДКЧЎЈНфФӘБҝҙЛФҠ(shЁ©)Ң‘ЧФјәЗпИХөДёРКЬЈ¬Кг°l(fЁЎ)БЛИҘҮш(guЁ®)‘Саl(xiЁЎng)өДНҙҝаРДЗйЎЈЩpОцЈә
ҹo(wЁІ)В•КЗЧоҙуөДұҜ°§ЎЈРБ—үјІЎ¶іуЕ«ғәЎ·Ф~ЦРУРЈә”¶шҪсЧR(shЁӘ)ұMіоЧМО¶Ј¬УыХf(shuЁӯ)ЯҖРЭЈ¬УыХf(shuЁӯ)ЯҖРЭЈ¬…sөА“МмӣцәГӮҖ(gЁЁ)Зп”ҺЧҫдЈ¬ЛгКЗ°СіоҢ‘өҪБЛҳOЦВЎЈНфФӘАпҙЛФҠ(shЁ©)өДй_о^Ј¬ІЙУГөДТІКЗЯ@·N·Ҫ·ЁЎЈЖдЦР“іоөҪқв•r(shЁӘ)“ҝӮМбЈ¬ТФПВ·ЦҢ‘ХеҫЖЎўМфҹфЎўҝҙ„ҰЎўБчңIЈ¬ФҠ(shЁ©)ҫдІ»ФЩСФіоЈ¬ө«іоҫwЧФТҠ(jiЁӨn)ЎЈФЪЯ@·NөШ·ҪЈ¬РБФ~УГХf(shuЁӯ)Ф’ұн¬F(xiЁӨn)Ј¬НфФҠ(shЁ©)УГ„У(dЁ°ng)Ччұн¬F(xiЁӨn)Ј¬ҝЙЦ^®җЗъ¶шН¬№ӨЎЈУЦЈ¬өЪ¶юҫдУГРБ—үјІЎ¶ЖЖкҮЧУЎ·Ф~ЦР“ЧнАпМфҹфҝҙ„ҰЈ¬үф(mЁЁng)»ШҙөҪЗЯB I(yЁӘng)”өДіЙҫдЈ¬ңҶИ»ФЩ¬F(xiЁӨn)БЛТ»ӮҖ(gЁЁ)Ҳу(bЁӨo)Үш(guЁ®)ҹo(wЁІ)йTөДЦҫКҝРОПуЎЈЦ»КЗҙЛФҠ(shЁ©)ФЩҫYТФ“ңIәЫЙо”ИэЧЦЈ¬п@КҫБЛТ»ӮҖ(gЁЁ)ҢmНўҳ·(lЁЁ)ҺҹФЪНцҮш(guЁ®)Ц®әуөДРДАн о‘B(tЁӨi)Ј¬ТСІ»ДЬәН®”(dЁЎng)ДкөДРБ—үјІПаұИБЛЎЈ
оhЎўоiғЙВ“(liЁўn)Ј¬Т»Ү@ЦӘТфЙЩЈ¬Т»Кг№Каl(xiЁЎng)ЗйЈ¬јИ‘Ә(yЁ©ng)о}Ј¬ұнГчЦ»УРНхХСғx·ҪДЬТэһйЦӘјәЈ¬УЦТФјТаl(xiЁЎng)Ц®Лј°өФўНцҮш(guЁ®)Ц®НҙЈ¬п@КҫіцЧчХЯөД„“(chuЁӨng)ЧчТвҲDЎЈ“ю(jЁҙ)Ў¶ЙП№ИҝӨҲDҪӣ(jЁ©ng)Ў·Ј¬ьSҪрЕ_(tЁўi)ФЪҪсәУұұТЧҝh–|ДПК®°ЛАпЈ¬СаХСНхЦГЗ§ҪрУЪЖдЙПЈ¬ТФСУМмПВКҝЈ¬ЛмТФһйГыЎЈУЦЈ¬Ў¶ҳ·(lЁЁ)ё®ФҠ(shЁ©)јҜЎ·ҫнЛДОеТэЎ¶ҳ·(lЁЁ)Ф·Ў·ұМУсёиХЯЈ¬ЛОИкДПНхЛщЧчТІЎЈұМУсЈ¬ИкДПНхжӘГыЎЈоhВ“(liЁўn)З°Т»ҫдХf(shuЁӯ)ҝХУРьSҪрЦ®Е_(tЁўi)Ј¬әуТ»ҫдХf(shuЁӯ)НчХ{(diЁӨo)ұМУсЦ®ёиЈ¬·ҙҸН(fЁҙ)кҗКцөДјИКЗЧчХЯН¬НхЗе»ЭФЪФӘҙу¶јөД№ВјЕМҺҫіәНұҜҗнЗй‘СЈ¬УЦә¬УРЛыӮғқҚЙнЧФәГЈ¬І»ЕcФӘИЛЩFЧеәНЛОКТҪөҫЮӮғ?yЁӯu)йОйөДҲ?jiЁЎn)Ш‘№қ(jiЁҰ)ІЩЎЈоiВ“(liЁўn)ПИҢ‘ЗппL(fЁҘng)ЦРоқ¶¶өД“Иf(wЁӨn)И~”Ј¬ТrНР„eүф(mЁЁng)І»іЙЈ¬ФЩУГ№ВҹфТ№УкТrНРҡwПўлyҪы—-ЧФИ»Ј¬Я@АпөД“№Каl(xiЁЎng)РД”ұнЯ_(dЁў)өДИФКЗҢҰ(duЁ¬)ЛОКТөДЧ·ДоЎЈҢ‘·ЁЙПЈ¬З°ғЙҫдУГөд№КЦұКгРШТЬЈ¬әуғЙҫдУГӯh(huЁўn)ҫі·ҙТrаl(xiЁЎng)РДЈ¬КЦ·ЁЧғ»ҜЈ¬Р§№ыҳOәГЎЈ
Д©В“(liЁўn)№КТвеҙй_Ј¬УЙКгЗйЮD(zhuЁЈn)ИлҢ‘ҫ°Ј¬УГОаН©УкЎў„ЕҡвҳӢ(gЁ°u)іЙЖаЗРұҜӣцөДТвҫіЈ¬һйЙПОДЦРТСҪӣ(jЁ©ng)бjб„іцҒн(lЁўi)өДёРЗйФO(shЁЁ)УӢ(jЁ¬)БЛҙуЧФИ»өДЙоіБ»Шн‘Ј¬Тт¶шК№ЧчХЯөД“қв”іоУРідТзә®ҝХЎўЗЦБијЎДwЦ®„Э(shЁ¬)ЎЈ
АоүәБЦЎ¶әюЙҪоҗГШЎ·Хf(shuЁӯ):“…ЗУСНфЛ®ФЖіцКҫЎ¶оҗёеЎ·јo(jЁ¬)ЖдНцҮш(guЁ®)Ц®ЖЭЈ¬ИҘҮш(guЁ®)Ц®ҝаЈ¬ЖDкP(guЁЎn)іоҮ@Ц® оӮдТҠ(jiЁӨn)УЪФҠ(shЁ©)ЎЈОў¶шп@Ј¬л[¶шХГЈ¬°§¶шІ»Ф№Ј¬ёиЖЫ¶шұҜЈ¬ЙхУЪНҙҝЮЎЈ”»Х”Еc“қс”Ј¬ л[ЕcХГЈ¬ұҫҒн(lЁўi)КЗ»ҘПаҢҰ(duЁ¬)БўөДЈ¬ө«Л®ФЖ(ФӘБҝМ–(hЁӨo))Әҡ(dЁІ)ДЬ°СЛьӮғәНЦCөШҪy(tЁҜng)Т»ЖрҒн(lЁўi)Ј¬РОіЙЧФјәМШКвөДЛҮРg(shЁҙ)пL(fЁҘng)ёсЎЈҫНЯ@КЧФҠ(shЁ©)¶шСФЈ¬ЖдЦР“ЙЩЦӘјә·Ц”Ўў“ҝХәГТфЧo(hЁҙ)”Ўў“№Вр^үф(mЁЁng)”Ўў“№Каl(xiЁЎng)РД”өИөИЈ¬ҺЧәхҝЙТФХf(shuЁӯ)КЗЗ§°ЩДкҒн(lЁўi)ұ»ОДИЛҢW(xuЁҰ)КҝӮғіӘ ҖБЛөДкҗФ~Ј¬Тт¶шИЛӮғҝЙДЬХ`ХJ(rЁЁn)ЛьКЗТ»КЧөИйeЦ®Чч—Я@КЗҙЛФҠ(shЁ©) “п@”Еc“ХГ”өДТ»ГжЎЈө«Из№ыЦӘИЛХ“КАЈ¬ЙФЧчЯM(jЁ¬n)Т»ІҪөДҝјІмЈ¬ДЗГҙНфФӘЦ»ТӘФёТвЕКёҪФӘіҜРВЩFЈ¬„t“ьSҪрЕ_(tЁўi)”ұШІ»ЙхЯh(yuЁЈn)Ј¬№Каl(xiЁЎng)ТІҝЙ“ҳs”ҡwЈ¬УЙҙЛУЦҝЙ”а¶ЁЯ@КЧФҠ(shЁ©)ЦРөДЦӘјәЦ®Ү@Ўў№Каl(xiЁЎng)Ц®ЛјҪ^І»ДЬЧчНЁіЈТвБxҒн(lЁўi)АнҪв——Я@УЦКЗҙЛФҠ(shЁ©)‘л[”Еc“Оў”өДТ»ГжЎЈЧчХЯәҶ(jiЁЈn)ҪйЈә
НфФӘБҝЈЁ1241Ў«1317ДкәуЈ©ДПЛОД©ИЛЎўФ~ИЛЎўҢmНўЗЩҺҹЎЈЧЦҙуУРЈ¬М–(hЁӨo)Л®ФЖЈ¬ТаЧФМ–(hЁӨo)Л®ФЖЧУЎўіюҝсЎўҪӯДПҫлҝНЈ¬еXМБЈЁҪсХгҪӯәјЦЭЈ©ИЛЎЈ1288ДкЈЁФӘКАЧжЦБФӘ¶юК®ОеДкЈ©іцјТһйөАКҝЈ¬«@ДПҡwЈ¬ҙОДкөЦеXМБЎЈәуНщҒн(lЁўi)ҪӯОчЎўәюұұЎўЛДҙЁөИөШЈ¬ҪKАПәюЙҪЎЈФҠ(shЁ©)¶ајo(jЁ¬)Үш(guЁ®)НцЗ°әуКВЈ¬•r(shЁӘ)ИЛұИЦ®¶ЕёҰЈ¬УР“ФҠ(shЁ©)К·”Ц®ДҝЈ¬УРЎ¶Л®ФЖјҜЎ·ЎўЎ¶әюЙҪоҗёеЎ·ЎЈ